文 / 蛰惊
一
卢生是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,他家老房子就在我家屋后,我们从出生起就认识,夏天一起捅过鸟窝,秋天一起爬树摘山核桃,冬天沿路滚过雪球。我们俩是寨子里出名的调皮捣蛋鬼,为此,我们没少挨过打骂,七岁时跳到邻居家水池里捉鱼,被抓住处罚,跪在院门外整天;八岁时丢石子打碎了寨里人家玻璃,被主人家押犯人般压到家里要求赔偿惩罚;九岁时把别人家的小孩打得脸肿,被其父母骂得狗血淋头。
卢生从他爷爷到他三代单传,所以祖宗几代留下来的传宗接代、光宗耀祖的祖训落在他的身上。每一次闯祸后,他必被他父亲禁足两天不准出门,我都会悄悄的从他家后院墙翻进去,再从院里的香樟树上爬到他的窗前,在阁楼上我们商量去哪里捉还在学习飞翔的的小鸟,去摘哪家院子里的果子……
小学五年级的寒假,卢生和我在村北的歪脖子树下比谁撒尿撒得远,正撒到一半时,他舅舅急急忙忙跑来,一把拽着他往回走,边嚷着骂:“你狗日的还有心在这撒尿,你老爹他妈的都挂了。”
那时我不知道挂了是什么意思,提着裤子跟着他们。到他家时见院里用长凳搭起一块门板,他老爹全身是血躺着上面,他母亲趴在旁哭得死去活来,卢生低头跪在边上,握住双拳像在忍住什么,冬日里的斜阳把他瘦小的身影拉得很长,像个奋力爬行着的蜗牛。
那天以后,卢生就变成了别人家的乖孩子,不在和我跑出去疯玩,而是认认真真的上学、写作业、做试卷、回答老师提问,空闲的时候帮母亲做饭、浇灌菜园里的蔬菜,赶牛上坡,饲喂猪圈里面的黑猪。由于以前我们一起得罪了不少寨里同龄人,其他小伙伴自然不愿意和我玩,我也觉得他们无趣,一个人也捣不了什么蛋,在卢生第20次拒绝和我一起出去谈弹珠时,我站在他家院门前,看着他转身提起一把菜刀斩菜叶喂猪,专注而用力。我突然也想做一个乖孩子,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,只有这样,才可以和卢生一起玩。
卢生的成绩越来越好,从六年级到初三,成了学校的传奇人物,也越来越受老师、同学欢迎,特别是女同学。
当然也有人例外,比如苏小秋。苏小秋长得漂亮,做的事情也出格,头发染了颜色,还画个淡淡的眉,在所有老师眼里,她是个名副其实的差生,是教育学生的典型负面教材;在所有学生眼里,她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另类,毫无交集的同学。苏小秋与全班人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的,她对所有人都冷眼相对,包括卢生。
但是初三时,班主任把苏小秋安排和卢生同桌,让卢生帮忙苏小秋提高成绩。
那时候我和陆霁同桌,她在自习课上用笔敲我手臂,我转过头去,问她做什么?陆霁用手指左前排的卢生和苏小秋,我顺着看过去,只见他俩不知道在悄悄说什么,苏小秋时不时在卢生耳边说几句话,卢生便笑了。
陆霁说:“苏小秋喜欢卢生?”
我不以为然:“你又在瞎八卦什么?”
陆霁凑到我耳边说:“你不是女生,你不懂。”我听了没当回事,低头继续写作业。
二
毕业班周末补课,上午课程结束,我和卢生正在教室复习刚学完的二次函数。有人在走廊上呐喊吵闹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一个同学跑进来,说:“出事了,苏小秋被人拦住了。”
我一听是苏小秋,平时没什么来往,便没了管闲事的兴趣。卢生抬起埋在书本间的头,匆匆忙忙跑了出去,我纳闷了一下,也跟着出去。只见几个差班的混混将苏小秋围在去食堂的路上,伸手伸脚的乱来,这几个人大家都认识,全是镇上的,仗着是地头蛇平时爱欺负学生,当时古惑仔火爆得一塌糊涂,学校混日子这帮学生自然学着拜把子,成立帮派,抽烟喝酒、打架斗殴。
卢生操了一声,喊:“狗日的些,干什么?”
几个混混围过来,推了推卢生的胸膛,说:“你妈的杂种,走开,不关你鸟事。”
卢生抬手一拳打在正面混混的鼻子上,混混些哪里受过这种待遇。发起横来扇他耳光,踹他腹部,我正跑过去帮忙,卢生往食堂跑去,不一会儿,提着一把菜刀冲过来,一刀砍去,一个混混被砍到手臂,混混们慌了神,一窝蜂跑了,卢生提着菜刀,满校园追着混混头,那天我仿佛又看到他提起菜刀斩菜叶的时候的情景,专注而用力。
这件事的影响很恶劣,混混家长全跑到学校讨说法,卢生被勒令退学。他母亲跪在校长办公室求情,卢生站在外面走廊上,低着头,双拳握得紧紧,把指甲都握进了肉里。
他最终还是退了学,就在离中考还有四十一天的时候。他收拾完书籍铺盖,我们一起站在教学楼的天台上,晚风吹起他额前的头发,我们点了一支烟,他说:“我爹的遗言,就是让我好好读书,传宗接代,光宗耀祖。”
我感到心里闷,猛烈吸了一口。
他长长地吐出烟雾。又说:“光宗耀祖我是做不到了。”
我问他:“你当时为什么要拿刀冲上去?”
他一口吸完,挥臂远远的扔掉烟头,说:“不知道,可能是当年那泡尿没撒完?”
我把烟头扔地上,一脚踏灭,问:“要不要再比一次。”
他说:“来啊,正好分出胜负。”
我俩站在栏杆前,鼓着劲往下撒,楼下教室内有人喊:“下雨了,靠,下两根水柱。”
我们听了边撒边笑,正在这时,后面突然有人喊:“你们在干什么?”
我一听是苏小秋的声音,吓得急忙用力憋,饭吃到一半可以不吃,尿撒到一半还真憋不住,残留滴了几滴。卢生这小子可没有管苏小秋,犹自撒完了才慢慢拉紧裤链。
苏小秋骂了声:“流氓。”
卢生转过身,看着苏小秋说:“太他妈爽了。”
苏小秋噗呲一笑,说:“卢生你这个书呆子,背地里臭流氓。”
苏小秋接着说:“你出来,我有事给你说。”
卢生:“苏大小姐,我可要回家放牛了,有事就在这里说。”
苏小秋:“放你妹,给老娘滚出来。”
卢生屁颠屁颠的走出去,苏小秋仰着头说:“我喜欢你。”
卢生张大着嘴,半天合下来:“苏大小姐,你用不着以身相许的,如果你有愧疚感,就好好念书了,把我的也念完更好。”说完他摆摆手,走了。
苏小秋在后面喊:“卢生,你记住,我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。”
三
夏天结束的时候,我们都从乡镇上考进城里高中,苏小秋和我同校不同班。卢生也进了城,不过他是在城北一家超市做服务员,我去找他,他刚卸完货,满头大汗的站着,外套缠在腰上,宁宁在旁边给他递脸帕和水,他接过脸帕擦完脸,仰着头咕噜咕噜喝完一瓶水,宁宁笑着接过脸帕和空水瓶,这一幕每天都在学校操场上上演,不过换成的打篮球的男孩子和在旁呼喊的女生。
宁宁是超市的收银,他不知道怎么勾搭上她的。
我们在他下夜班后在超市买了罐装啤酒,坐在城北广场的石阶上喝,空瓶子就随手丢,让它沿着台阶咣当咣当滚到草坪上。
我问:“苏小秋有没有找过你?”
他说:“你说她是不是疯了,跑到超市说要做我女朋友?”
我说:“苏小秋挺好的。”
他一口气喝了一罐,站起来说:“她只是愧疚,你知不知道我和她有过节。”
我说:“不知道。”
他说:“有一天中午在食堂,我排队恰好排在她后面,人山人海的,我的手不知道怎么碰到她屁股了。”
我好奇,问:“就这样?”
他说:“你别打断我,我那时正想说对不起,听见她小声骂我“臭流氓,癞蛤蟆”,我气不过,质问她你骂谁呢?她大声说就骂你这个色狼,当时所有人都听见了,齐刷刷地看向我,别提我多火冒了,我一怒之下,伸手在她屁股上使劲捏了一把。”
我说:“你也真够流氓的。”
他说:“既然背了这骂名,就不能白白的背。那件事以后,她见到我就像见到瘟神似的。开什么玩笑,她能喜欢我?”
我说:“你怎么拒绝她的?”
他使劲拉开一罐啤酒,酒花嗤嗤冲出来,他说:“宁宁当时在旁边,我就指着她说,我女朋宁宁,她咬牙切齿地瞪着我,转身走了,再也没有来过。”
我突然找不到说的,这时宁宁来接他,在草坪里踢啤酒罐。
他说:“宁宁就这样和我在一起了。”说完他走下去牵着宁宁的手。
我看着他那么笃定的眼神望着宁宁,我喉咙里冒出来的关于苏小秋的话又深深地吞了回去。我没有告诉她,苏小秋成为了我的好朋友,她一改曾经的反叛,头发剪成了齐颈短发,穿着大一号的蓝色校服。学习起来比谁都努力,无数次的跟我说要把卢生那一份也学回来,每次遇到我都会问起他。
他怎么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情了。
有时候爱情就像六月的雨,你以为不会来的时候,顷刻之间便轰然而至,你要么找把伞遮挡,要么找个屋檐躲避,又或者让它把你淋成个落汤鸡。
三
高中学业越来越紧张,卢生也越来越忙,我们再也没能在午夜喝酒。高考后我离开那座城市,到山城一呆就是六年。苏小秋去了杭州,毕业后留在杭州一家银行。
卢生后来去学理发,再后来他和宁宁南下广州打工去了,我们断了联系。
去年国庆我邮箱收到一张电子请柬,是苏小秋的婚礼邀请,男方我不认识。在这之前两月,我到上海参加一个博览会,回程绕道杭州去看她。她带我到周庄去。
我们租了一条游船,划船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船夫,穿个背心,露出黑釉色的皮肤。开始她总要自己学着划,船夫在旁讲解如何摇动木橹,她都只能让船原地转圈。无奈之下,她只好把木橹还给船夫,船夫轻轻摇动木橹,撩起艳漪丽波,小船悠悠荡荡地驶入河心。
我们已经五年多没见,那天她穿了条白色棉长裙,站在船中,身材高挑,面容沉静,像个女王,让人再也看不出初中时苏小秋的模样。
毫无意外,她向我打听起卢生的现状,我只能摊摊手,我和他也已经失去联系数年了。
我说:“他多半已经结婚了吧!”但说出来我就后悔了,又忙说:“也许也没有”。
我见她眼里的光明显暗淡了下,动容后露出惆怅。我安慰说:“你不用背着包袱的…”
“我认识他好多年了,十一年、好像还没有,十年多吧!”她打断我的话,我不知道她想说什么。
“那时候他像个好学生,是班上女生私下里谈论的话题。我对那些女生不屑一顾,自然也觉得他们谈论也不过是个书呆子罢了,但听得多了,也曾忍不住好奇心,偷偷观察过他,他真是无比认真,专注得很,遇到难题的时候轻轻皱着眉头,解决了又轻轻舒展开来,让人看着突然也想和他一起高兴似的。”她喃喃说起。“我以为他是个和其他人不同的人,至于哪里不同,我也说不上来。那时学校同学都看我不起,认为我是个坏学生,水性杨花什么的,他们以为谁都可以占我便宜,对这些我又何曾在乎过。我没有想到的是,卢生也是那样的人,有天在食堂,他居然对我动手动脚的,我突然觉得他也不过是个伪君子,大尾巴狼而已。”
我说:“那天他提刀追着那帮混混也许就是想证明他不是个混混,不会干流氓做的事情。”
她说:“自从和他同桌之后,我就知道他不是流氓了,他那时候对我的成绩很上心,替我补数学和英文,我成绩提升就是那时候开始的。想起我们同桌,我最喜欢给他讲我看来的各种笑话,看着他在自习课上想笑又不敢笑的表情,那时候觉得真过瘾。想在想来,也许在我偷偷观察他的时候,我就喜欢上他了。因为在乎,心里才会失落,才会喜欢作弄他。可他宁愿喜欢那个宁宁也不喜欢我,我就那么讨他厌烦。”
我正想该不该给她说宁宁的事。她又说:“高二的时候,我寄住在舅妈家,有晚自习后,我嫌大路远,便走进路穿巷子,在一条黑巷子里有个围着面的人拦住了我,他叫我把钱拿出来,我脚都吓软了,只好把钱给他,他还不满意,这时巷口突然有个人骑自行车朝着他冲进来,围面人被撞翻后爬起来跑了。自行车上的人也摔在地上,他爬起来疼得哎呦一声,我一听居然是卢生那混蛋,我说你跟踪我,他说你就自美吧,谁跟踪你。说完又疼得哎呦一声,双手手捂住右脚,我给你坐下来,我帮你看看伤到哪里了。他白我一眼,还用看吗?伤到脚了。我说废话,坐下来。他哦了一声,乖乖的坐着。我给他掀开裤脚,见他膝盖被磨破一大块,鲜血淋漓,心里不由得有种想哭的冲动。”
我听她现在说起来起来轻松,可以用想象要不是卢生出现当时场面是多么危险。
但我也感到我好奇:“他是不是每晚都悄悄护送你,怎么那么巧合?”
她说:“他百般解释说他晚班后路过,可那个巷子那么偏远,他也没住那个方向。那晚我陪他去药店买了外伤药,他坚持一瘸一瘸的送我回去,到楼下时,他举手摸摸头,我说今晚谢谢你,我上去了。他张了张口,像是有什么话说,可又没说。我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儿,我说我真上去了。他说哦,以后别一个人走那么黑的巷子。我转身走了,他在背后连续说了三次。我转身说知道了,你烦不烦。他笑了笑,说是挺烦的。你不知道,那晚是我这么多年最高兴的一晚,我以为第二天晚上还能看见他,可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。”
我心里忽然浮现出这个画面,一个男孩瘸着腿,在行人的诧异中,推着俩撞歪的自行车,在路灯的昏黄色中,陪着那个女孩走着,他一定心里有很多话对她说,也许还想张开双臂紧紧抱住她,可到楼下时,他都只是重复说了三遍那句不要一个人走那些黑巷子。
船到岸边,她抬头望着岸边的行人来来去去,哽咽着说:“我心里喜欢他,惦记着他,他却怎么都不信,我一直做的无非是想让他相信而已。”
国庆我参加了苏小秋的婚礼,婚礼办得隆重而盛大,苏小秋穿着洁白色的婚纱,挽着新郎官的手,浅笑着和来宾打招呼。如今的她,美丽动人,魅力大方,丈夫也高大帅气,爱她胜过爱自己。我坐在下面,看着他们交换戒指、拥抱、轻吻,想起高中时去看卢生的场景。
那时候他已经改学理发了,但没有穿上发廊特有的紧身裤、尖皮鞋,头发依旧是短短的黑发。
那时候他和宁宁租住在一所监狱旁边的小巷子里,那栋楼四面围合,中间有个天井,他们住在二楼,光线很不好,白天也如同黑夜。
宁宁没在超市收银了,换了工作去电影院售票,常常上夜班。
那天恰好她上的是白班,下班后买了菜提着回来,卢生下楼去接她。
卢生炒了几个菜,我们三人围着吃。卢生说:“等我把手艺学到手,就去物色个门面,开间理发店,到时候宁宁过来帮忙打理,好过给别人打工。”
宁宁笑着打趣:“那你得学快点,我做梦都想当老板娘呢?”
我说:“那我以后的发型就包给你了,要是找不到女朋友,你可负责。”
卢生说:“找不到女朋友关我什么事?”
我说:“证明你理发手艺不行啊。”
卢生说:“那合着来找我理发的人都不能单身啊,人丑就应该多读书,光理发起个毛用。”
宁宁在旁笑得合不拢嘴,说:“卢生,那怎么不见你多读书啊!”
卢生鄙视她一眼,说:“我有女朋友啊,用得着吗,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追我的。”
宁宁用手掐他,说:“滚,卢生,没见过你这么脸皮厚的。”
我看着他们打闹,那时候觉得所谓人间烟火,不就是嬉笑平常,满怀希望吗?
四
三个月后的春节,我回故乡,母亲说:“卢生也回来了,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。”我说:“我去他家看看。”
我转过小时候做过的小路,几步就到他家院里,他母亲正在院子里腌制腊肉,看见我,高兴地说:“小野回来了,快到屋里坐,小生也回来了,你们俩几年没见过了吧。”
我快步走向屋里,他可能听到母亲的话,也起身准备往外走,看见我,他满含激动,问:“什么时候回来的。”
我说:“刚回来,你丫这几年跑哪里去了?怎么都没和我联系。”
他说:“一直在广州的,手机掉了几次了,把你号码都弄丢了。”
我说:“不有QQ吗?”
卢生说:“我很少用那玩意。别说那么多了,快进来坐。”
我们俩坐着屋里,聊了很多他这些年的境况,先是理发学得差不多的时候,没本钱开发廊,只好和宁宁去广州打工,挣点本钱,还好有门手艺在身上,他去理发店做技师,宁宁去工厂上班,几年下来存了一些钱,这次回来准备开店,再把婚结了。
聊了半天,我觉得要告诉他苏小秋结婚了这个事情,我说:“苏小秋结婚了。”
他很平静,说:“国庆的时候吧,我知道。”
我问:“她给你说了吗?”
他说:“没有,我自己知道的,我关注了她微博,她每天都在上面分享她的动态。”
我问:“当年你为什么拿着刀冲上去。”
他没有回答我,沉默了会儿说:“年轻时谁不曾深深喜欢着一个人。”
我说:“你总算承认了。”
他沉默了会儿,长长的叹息了一声:“我喜欢她又有什么用?”
我说:“可她也喜欢你啊?”
卢生说:“我知道,可两个人并不是因为喜欢就能在一辈子啊,你看我再怎么努力奔波,我的顶点也在那里。可苏小秋不一样,她本来就可以遇到一个更爱她,更有能力让她过好生活的人。她结婚前,我去杭州悄悄看过她,她过得很好,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这样,我也就更能好好爱宁宁了,她跟我受了那么多苦。”
他接着说:“很多时候我们没在一起,但我们几乎是在一起了的。”
有些话没说,并不代表心里没有。有些话涌到喉咙,又终吞了回去。我们说不喜欢你,好像我们真的从来没有喜欢你一样。但很多时候我们没在一起,却几乎是在一起了的。因为我坚信,你过得很好,比在我身边重要。
 点击收藏
阅读(3,682)
鹿印(1)
点击收藏
阅读(3,682)
鹿印(1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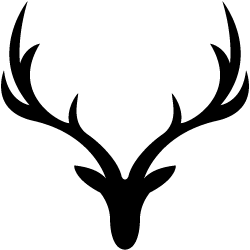


坚持做一件事情,真的很难,但坚持喜欢你,我做了很多年。